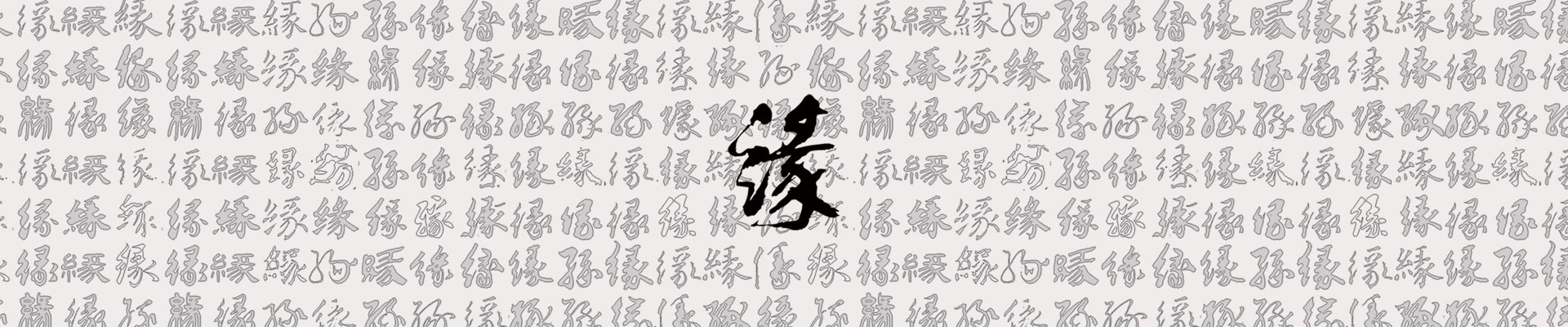今世缘·同题共写父亲母亲丨父亲的高光时刻
发布日期:2025-09-23 浏览次数:777
父亲是一个农民。父亲一生当中,也有他认为的高光时刻。作为他的儿子,对于他的过往经历,我认为至少有两件事应该让他引以为荣。前一件事,他很少提及,却被村里的很多人经常提起。后一件事,他经常提及,却被有些人不屑一顾。
父亲是1948年生人,在他年轻的时候,经历过多种磨难。我从小就听他讲过,当时那个年代的种种不易。
父亲高小毕业。在那个年代,在村庄里算是有文化的人。后来,大队让他干生产队长。再后来据说还干过几年生产队会计。
在我看来,父亲的高光时刻,就是他干生产队长的那几年。我出生后没几年,就分田到户了,父亲也不干队长了。在之后的几十年里,父亲从来不跟我提他当年干生产队长和会计的事情。倒是老家的邻居,还有我爷爷活着的时候,经常跟我讲起父亲当队长的那段日子。
在他们眼里,我的父亲就是一个闲不住的人,是一个只知道拼命干活的人,是一个六亲不认的人。父亲干生产队长的那几年,还是大集体。父亲活紧,天没亮就吆喝生产队的队员们起来去地里干活。一个邻居大叔跟我讲过,你爹当队长那几年,可把咱们四队的社员撵毁了,有时候才半夜,鸡还没打鸣他就挨家挨户让社员起来去地里干活。有时候干了半晌活,天还没亮。那时候,社员人人心里骂你爹,骂他是半夜鸡叫周扒皮。
就在我一脸难堪的时候,邻居大叔说,后来,我们才明白,你爹做得是对的。那段时间,经常下雨,地里种的红薯如果不及时刨回来,就得烂在地里,那么我们社员就没有东西吃了,就得挨饿。咱们庄有一个生产队,就是因为没及时刨红薯,大都烂在地里了,那个生产队的社员都可羡慕咱们队了,大家伙心里都明白,嘴里唠唠叨叨嫌起得早赶得紧,心里都说你爹的好,如果不是你爹当队长活赶得紧,咱队社员那几年说不准得挨饿。
之所以说父亲六亲不认,也是他当年干生产队长的时候一些让人不理解的行为。据说父亲干生产队长和生产队会计的时候对自己的要求很严,不是自己的东西坚决不拿,公家的东西坚决不碰。生产队里的一根柴火棒子,都是公家的,坚决不能往家里带。听说有一次,我们四队社员从田里干活回来,我二叔那时候才不到二十岁,饿极了,偷吃了生产队的一根红薯,被父亲发现了,我父亲当着那些社员的面揍了二叔一顿。父亲后来从家里拿了生产队分的一根红薯放到生产队的仓库里。我的二叔,父亲的亲弟弟,当时委屈得难受,回家就跟我爷爷奶奶告了父亲的状。父亲回来,爷爷奶奶也没有埋怨父亲,只是让他以后揍二叔下手轻点。这事被我老家生产队的老百姓说了几十年。每当提起我父亲的时候,他们就说到弟弟偷吃生产队的红薯被当生产队长的哥哥暴揍的故事。
多年以后,我听到了这个故事,望着蹲在屋檐下晒太阳的父亲。父亲沟壑纵横的脸上,流淌着岁月的痕迹。我忽然有种泪目的感觉。这么多年来,我在外打拼,也在多家单位干过负责人,手里也曾有过一些小权力。但是我始终秉承父亲做人的原则,不是自己的东西坚决不拿。有人说我装清高,但是,父辈坚守的原则,我坚决不会改变。事实证明,父亲当年坚守的原则是对的。我认为,父亲干生产队长的那段岁月,理应是他人生中的高光时刻。
父亲到了晚年,绝口不提当年干生产队长和会计的那段日子,倒是经常和人聊起他带人挖藕的经历。
父亲六十岁以后,再去建筑工地找活干,人家就不愿意要他了。那时候,我已经进城工作,我曾经劝过父亲,不要再出去干活了,就守着家里的几亩田吧。我给他买了唱戏机,让他没事的时候听听。父亲却闲不住,庄稼地里的活干好以后,他开始重操他的老行业。不过这次,父亲是找了十几个人一起干,当起了挖藕队队长。
他带着那些乡亲奔忙在十里八乡,甚至外省,整整挖了近十年藕,直到他年近七十,由于腿疼得受不了,才罢手歇工。我没有问父亲,我曾问过母亲,父亲作为挖藕队的队长,工钱一定会从中提一部分吧?
母亲哼了声,一分钱不提,都是跟那些人平均分,就是这样,还没落好,还被人说闲话。
我问母亲怎么回事?
母亲说:“住在咱们东边的小六,跟你爹挖了好几年藕,有一次,就因为几块钱的零钱没法分,他还跟其他人说你爹贪了那几块钱。实际情况是,你爹用那几块钱买了一盒香烟分了给他们抽了。”
我当时就愣了,哎,父亲这些年,累死累活,联系雇主,搭了那么多电话费,还没落好。真是人心隔肚皮。
后来父亲解散挖藕队,不再出去承包挖藕,村里有很多人都认为是父亲生了小六的气,其实不是,父亲那段时间,腿疼,再加上一些其他老年病,他不能再下水浸泡了。
父亲不挖藕以后,他带的那些人,曾经有几个人想单独成立挖藕队出去包活干,却是对承包的藕田看不透彻,挖到后来因挣不到什么钱而解散。
父亲后来因为一次赶集回来,骑电动车摔倒,大胯摔断,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,回到家休养了大半年,能下床走路了,还是走不利索。村里父亲的发小来看父亲,父亲坐在院子里,跟他们聊天。聊他们小的时候一块玩耍的场景,聊各自的子女,聊身体状况,聊村庄里的同龄人哪些人走了。后来就聊到带人挖藕的事情。
父亲当时歪斜着身子,坐在院子里,脸上渐渐有了光泽,他嘴里连连吸着气:“当时挖藕,在咱们这一带,都挖不过我们。山东的种藕大户不知道从哪要到我的电话,打电话来找我们去给他挖藕。”
父亲跟他的那些发小絮絮叨叨聊到这些的时候,他不曾想到,在他的儿子心里,父亲的高光时刻,应该是他当年干生产队长的那几年。
在我小的时候,我和父亲母亲还居住在两间土坯房里。我永远记得我家靠近门旁的土坯墙上,有父亲用毛笔写的几个字,其中有两个字是我老家村庄的名称。另外几个字是“为人民服务”。
(文|王文钢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