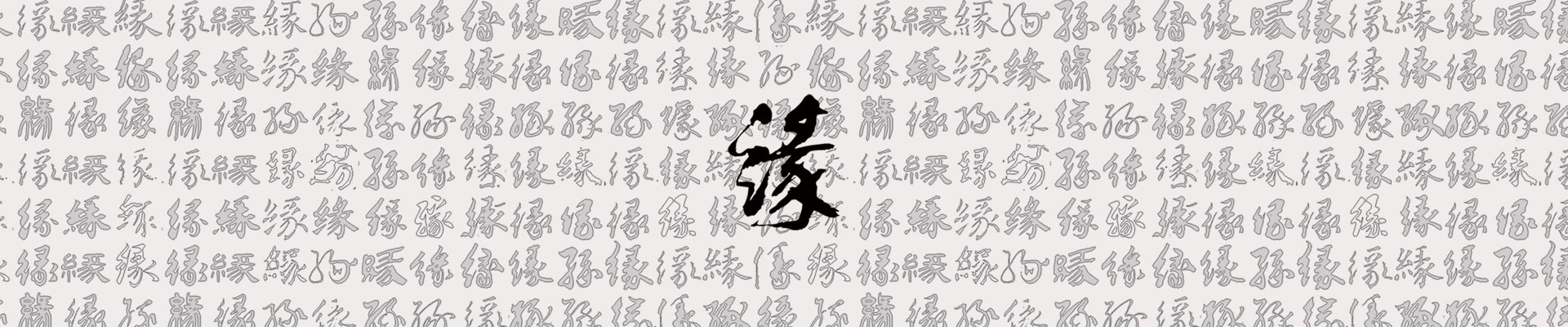今世缘·同题共写父亲母亲|父亲的背影
发布日期:2025-08-08 浏览次数:961
浙江西南的大山,我总觉得它在等着我来。
进入丽水境内,“绿巨人”宛如一条青龙舞动在连绵的崇山峻岭间,我曾经在云和、龙泉、庆元等地生活过的印象鲜活了起来。十八岁那年我参军入伍时,立在群山背影里目送我远去的父亲,这些记忆又一次浮上心头。
模糊又清晰,那是父亲留在我情感记忆中唯一温暖的画面。多地辗转、哪里需要哪里搬,“素其位而行”、勤勉敬业……记忆中父亲与我们聚少离多,除了这一次,我实在想不起还有任何其他送别的场面。
父亲是丽水人。他16岁加入浙南游击队,后被编入第三野战军,参加了解放战争。著名的上甘岭战役中也有他英勇的身影,其时,父亲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二军麾下的一个卫生兵。多年前河北卫视在做一档“缅怀英雄先烈·铭记革命情怀”的节目,编导杨先生读到了北京《劳动午报》上我写的短文《父与子》,辗转联系上我之后,要我提供更多详细的信息,遗憾的是我不能够——父亲光荣且值得自豪的履历,他从未与我们讲起过。
大约10岁我才回到父亲身边。此时他已去了偏远乡镇森工站下面的一个工段“思想改造”——那是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。见到身材魁梧的父亲迎上来想抱一抱我时,我一个劲地往母亲身后躲,“这是你爸,快叫爸爸。”看到母亲的眼泪流了下来,我被吓得哇哇大哭。许多年后我还管他叫“叔叔”。
幼年时我就和弟弟、妹妹随母亲一起被下放到与他相距200多公里的异地农村。其间我曾给他写过信,还记得抬头一行是:亲爱的爸爸——冒号。说实话,就那时而言,父亲对我来说只是个符号、远方虚幻的存在。也许想象过他的模样,可我一点都不记得了。
很长一段时间,我与他之间真的没有什么父子感情,特别是姐姐夭折之后。当母亲抱着年幼的姐姐在山里的简易工棚嚎啕时,父亲正带着一支采伐队在庆元的大山深处伐木砍竹。母亲说“他的眼里只有进度、指标和圆木、毛竹”——那正是新中国成立初期,百废待兴,社会主义建设热火朝天,祖国急需大量的栋梁、脚手架的时候……
其实我与父亲一起生活的时间并没有多长。搜索库存的记忆,有一回夜深雾浓,我拾菇迷失在了山里,被母亲和邻居们举着火把找回时,他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开会。后来有一次,只因为带了一打单位的信封给妹妹——那时候她正在学习写作、四处投稿,被父亲知道了,他令我端端正正地坐在对面,结结实实给我上了一晚上的课,从公私分明说到防微杜渐,他告诉我,魔鬼就藏在细小之处。而此时我已从部队退役,在地方工作了。
在得知我的女儿圣安德鲁斯大学研究生毕业后想留在国外工作,他特地大老远把我叫回去训了一顿,严厉批评我放任女儿而缺失了思想教育。说读了那么多书,学了本事应该回来报效国家。每逢人生关键路口的选择或家庭重大决定的时候,父亲总会迈着军人的步伐向我走来,提纲挈领、思想深邃,坚毅的神情让人不得不肃然起敬。
胸怀大义,正言厉色,公而忘私,清贫廉洁,他貌似无情的背后不是冷酷。淡泊守志,行而致远,抗美援朝战场上被敌军燃烧弹烧伤的大腿更加让他走得有板有眼,是嵌在他头颅深处一直不能取出来的敌机弹片使他百折不挠、有了铁一般的性格吗?多少年之后当我终于看清楚他留在世上高大的背影时,止不住泪流满面。
真正走进父亲的内心,我用了大半生。百炼成钢、千锤成器,多少年之后我才懂得那是爱的另一种表达。人生的道路漫长且曲折,如果说我的人生还算成功,父亲不断地敲打功不可没。
临窗而坐,遐观远眺,云峦起伏、千岩竞秀,曾经偏远的山区已成了喧嚣都市生态自然的后花园。“一声呼啸化烟尘”,从弯弯绕的盘山沙石公路,到平坦宽阔的水泥高速公路,再到风驰电掣的城际铁路,诉说着社会巨大的进步与发展、时代的变迁承载着多少人的壮志豪情和奋斗故事。
有容乃大,无欲则刚,沉默在寂静里的大山有一种超然物外、淡泊从容的景象。日月如梭,大块文章、经纬纵横的织绣中闪动着凡人的微光。花开无声、叶落有意,人生如逆旅,我亦是行人,迤丽而远、一路上我想了很多,又似乎什么也没想。
跨河过桥,山一程水一程都通向内心,后知后觉的惭愧里有笃行而不倦、唯实励新的轨迹。还有什么不能释怀的?这一趟行程是我又一次对父亲深切的怀念。疏离纷扰世相、追寻内在安宁,一切过去了的都成了珍贵的回忆。
翻山越岭,列车已钻出了隧道,山高水长、对父亲不一样的爱戴涌来……
文|夏明